我的老父亲 ——张玉兰
我的老父亲
文丨张玉兰
刘和刚唱的一首:“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每当听到这首歌,我的眼睛湿润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似乎看到了老父亲满脸的灰黄和憔悴,看到了他被日伪军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身影,看到了他不停地劳作满身的泥巴,想到了他用一生心血和汗水,酿造了一坛陈年的古醇让我们享用终生……他常说:“采得百花成蜜后,为子辛苦为儿甜”回想我的老父亲,他生活的苦涩何止吃了十分哟!
穿越亘古的时空,我多次在梦境里看到一个在荒野中踽踽独行的身影,听到他那悲伤与叹息的声音,感受到日本鬼子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进行肆虐蹂躏!想起那一幕幕的惨状,想起父亲的艰辛,都是同一个感受——凝重。
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父亲被古溪据点的日伪军抓走,同村一起被抓的9个人中,有一个是农会主任,他们被关在一间破房里。日伪军将父亲吊打!父亲死活不肯说出农会主任的名字,他被打得体无完肤,再把父亲推到河里开了一枪,鬼子以为他必死无疑,结果父亲从河底挣扎着潜水逃到对岸草丛里……一个孤独的身影,在黑暗中爬行,被一个好心人救下送到家时,已经奄奄一息。上身没有了衣服,下身只剩下一条破短裤,全身伤痕累累。 当年的我虽然年幼,父亲死里逃生满身鲜血的惨状,深深地刻印在我童年的心灵深处。尽管岁月慢慢逝去,但在我心中永远是,“看不见的伤,抹不掉的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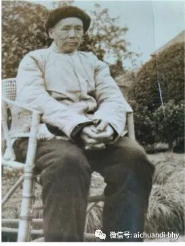
我的老父亲
长大后,又同被无情的大荒年折腾得饥寒交迫。我常在梦境里,看到父亲独自一人,在苍茫的暮色里翻地播种,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奔波在湿润微凉的秋风中。当父亲见到第二个出生的是儿子时,高兴得日不睡夜不眠为儿劳动。本村有一户做粮食生意的人家,父亲每日用一只木质独轮平车,装上满满的粮食,推送到四十里外曲塘镇上一家粮店,送到那里立马赶回,一回又是40里,半夜才到家,第二天一早再推送。过去叫替人家“推包车”,送多少拿多少钱。每天来回80多里的路程,双腿跑肿了,每晚回家再晚也得先将脚板底跑起了水泡放了第二天才能走。口渴了,在路边小河里喝点水;饿了,吃的自家带的玉米饼,从来舍不得买一分钱的东西解决一下辘辘饥肠。母亲劝他不要再推了,可他不听。他边走边用低吟近乎哭泣的声音打着别人听不懂的号子。在他走过的历程中,每一步都流下了斑斑的血迹和汗水,留下了激昂壮丽的脚印。在他的号子中,每一个音符都飞溅着血与泪的痕迹。
他不是哀叹个人的荣辱得失,是一家人的生活苦难,在煎熬着他那颗苍老的心。他抬头遥望美丽的天空,低头却置身在浑浊的深渊中。他常想:人死了能否上天堂?让高尚的灵魂在空中自由飞翔。他向上天求助,叩问着上苍,寻找着让凡人安居乐业的真理与希望,探索着生活的真谛与方向。他曾想过:要不是顾及上有老下有小,真渴望跨一步就去了前方的天堂!他纵情呐喊,举目张望,当年被日本鬼子强占的大半个中国,在这苍茫的大地上,哪里有他的救世主啊!这个踽踽的身影,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一个一米七五高的父亲,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今天看来如此之高大,如此之了不起,如此之受人尊敬!他默默地,不但将四个儿女培养成人,更了不起的将四个儿女培养成才:大女儿,大专,人民医院检验师、作家。大儿子,大学毕业。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兼职教授;二女儿中专,医院检验师;小儿子,军校团职干部、高级工程师(因工牺牲)。
这是一个伟大的父亲!看到父亲慈祥的面容,儿女们的良心在激烈地震颤,热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因为在他的一生中,只有无私的奉献,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就匆匆离开了我们。我万分遗憾,为“子欲尽孝而亲不在” 的遗憾。逝去亲情的伤痛,如钻入眼球里的木刺,触痛着我的心!
每每回忆起父母亲这段生话,总觉得这是一个严酷无情的话题,从懂事起,就听母亲讲述父亲如何为这个家庭苦苦的一生……当年卖去两只羊积攒二百元舍不得花,带给工作的儿子。
想起我的老父亲,心中无比的难过和酸涩。在我的脑海里,眼看岁月的风刀霜剑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年轮如沟壑盘亘于大地,历尽沧桑。我仿佛看到了他每一条皱纹里都深深地刻着人生的苦涩;每一滴汗水里,都浸泡着他一生的艰辛。然而,他那衰老而疲惫的目光里,依然充满着慈爱和期待,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们全家的脊梁。
我常常思索着他不朽的精神。虽然历史的悲剧大幕永远落下了,但我们应该珍惜新时代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是他们用苦难和汗水哺育着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踩在他们的肩膀上才能沐浴到辉煌的阳光,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享受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这和平、这幸福之路,其实就是他们用辛酸的泪水和血汗铺就的。
![]()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