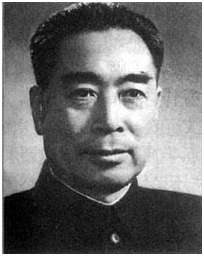《外公的“遗产”》作者:陆燕秋 点评:朱彪
外公的“遗产”
文:陆燕秋
外公于三年前在老家病逝,葬于村里公墓,成为千百个水泥墓冢中的一员。公墓面积很大,占地数十亩,入口在一条乡村小路旁,行人远远地就能看到。四周农田环绕,低吟的风吹来生者无尽的思念。外公身无长物,几乎没有什么遗产。
翻开家庭的老照片,一位中年人身穿白色的确良衬衫、青灰色西裤,头上戴着一顶草帽,黝黑的脸庞露出微笑,他正是我的外公。外公年轻时,是生产队里出了名的种田能手,寡言能吃苦,精瘦却有力,别人两天才能干完的活儿,他起早贪黑一天就能干完。
作家王安忆在《戏说》里曾写过一段话:“真正善于劳动的人,干活身上是一点不脏的。人不邋遢,活也不邋遢。”外公便是这样的人。印象中他只有几件白衬衫轮换着穿,不管是下田插秧打农药,还是挽起裤腿挑河泥,每当他披着一肩星光回家时,雪白的衬衫上几乎看不到泥巴。脚踩泥泞,也要把自己拾掇得清清爽爽,这是外公在我的童年留下的印象。
外公爱笑,笑声爽朗清脆,十米开外就能听见。每年小学暑假,我和表姐、表妹三人都会去外公家小住半月。只要听见远处爽朗的笑声,就知道是外公收工回来了,三人赶紧围坐桌旁,晃着小短腿儿喜滋滋地等着开饭。
外公哄小孩儿很有一套,每次收工回家,都会给我们三姐妹带回不同的惊喜。他种的土地就是他的“百宝箱”。别人家的田里只长谷物,可外公总会留出一陇田地,种上小孩子爱吃的枇杷、梨,甘蔗、香瓜、西瓜,光是桃树就有水蜜桃、蟠桃等五个品种。在那个物资并不丰裕的年代,他种的土地像一本童话,为我们的童年带来甜蜜的回忆。
爱笑的外公,还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仪式感,把生活和二十四节气挂勾。“日子要过得有时有节,有滋有味”,淳朴的话语里,他融合了一种传统的中式浪漫。立夏的鸡蛋、端午的粽子,冬至的汤圆、入秋的糖炒栗子,或者入冬的甘蔗,不同的时节,他都会骑着他的二八杠“凤凰牌”自行车,把东西送到我们三姐妹家里。风雨无阻。这一送就是二十九年。
后来他小中风,无法再骑车,便推着自行车挨家送。过了一段时间,自行车支撑不住他踉踉跄跄的双腿,他就拄着拐杖慢慢挪步,往往送完三家需要大半天的时间。家人出于担心劝他别送了,他不听,还是不声不响悄悄送。
外公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他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泥土气息的旷野长眠。他没有遗产,但是留下了很多足迹。脚踩泥泞,也要把自己拾掇得清清爽爽。把土地种成一本童话,为我们的童年带来甜蜜的回忆。笑声爽朗清脆,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仪式感。外公的这些“遗产”,让我真正长大了。
 作者简介:陆燕秋,如皋市公安局三级警长,曾担任如皋广播电视台《如皋警方》栏目主持人,原创系列短视频《小鹿姐姐说》多次被省级媒体录用,多次参加南通市级演讲、诵读比赛并获奖,被评为如皋市“三八”红旗手,被如皋市人民政府记三等功。
作者简介:陆燕秋,如皋市公安局三级警长,曾担任如皋广播电视台《如皋警方》栏目主持人,原创系列短视频《小鹿姐姐说》多次被省级媒体录用,多次参加南通市级演讲、诵读比赛并获奖,被评为如皋市“三八”红旗手,被如皋市人民政府记三等功。
【微 点 评】
朱 彪
在一本《读者文摘》里,我读到了这样的文字:“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事,见过一些人,才会明白我们认识的世界和生活是那么浅薄。于是我们就在那一刻,成长了。”巧合的是,散文《外公的“遗产”》也不约而同地提及了成长。
《外公的遗产》,经历的一些事其实很平凡,种田的外公,人干净利落,干活也干净利落。“不管是下田插秧打农药,还是挽起裤腿挑河泥,每当他披着一肩星光回家时,雪白的衬衫上几乎看不到泥巴”。
“外公哄小孩儿很有一套”,他开动脑筋把一小块地变成了“百宝箱”。枇杷、桃树,香瓜、西瓜……应有尽有。“他种的土地像一本童话,为我们的童年带来甜蜜的回忆”。
这还不够,外公还有另外的“绝活”。他能把平淡无奇的日子过出“仪式感”,不同的时令,变幻出不同的色彩。鸡蛋、粽子,汤圆、栗子等,点缀着童年的记忆。“风雨无阻,这一送就是二十九年”。
如果说上述的故事是一串珍珠的话,那么外公渐行渐远的足迹,就是一根连接珍珠的线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根曾经风华正茂的生命线渐渐枯萎了,但仍然在坚持。“自行车支撑不住他踉踉跄跄的双腿,他就拄着拐杖慢慢挪步”。
故事和人物形象交相辉映,“我”在外公的足迹面前渐渐学会了思考:一个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老人,生于斯,长于斯,把自己交给了土地,交给了秋天。他似乎没有遗产,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又似乎留下了很多,很多。
“脚踩泥泞,也要把自己拾掇得清清爽爽”,“把土地种成一本童话,为我们的童年带来甜蜜的回忆”,“笑声爽朗清脆,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仪式感”这些不是遗产的“遗产”,才是“我”成长的真正理由。正如作者所言,外公的这些“遗产”,让“我”真正长大了。
 评者简介:朱彪,如皋市作家协会会员。曾有作品发表于《中国散文诗》《散文诗》《诗神》《江海晚报》等。很怀念从前电台的《快乐旋律》,怀念《如皋日报》的“水绘园”,怀念《春泥》,那里是我青春梦想启航的港湾。
评者简介:朱彪,如皋市作家协会会员。曾有作品发表于《中国散文诗》《散文诗》《诗神》《江海晚报》等。很怀念从前电台的《快乐旋律》,怀念《如皋日报》的“水绘园”,怀念《春泥》,那里是我青春梦想启航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