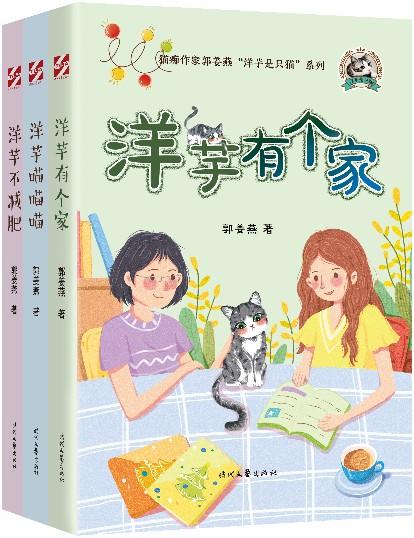陈曦霞作品《我不是二毛妈》
我不是二毛妈
作者:陈曦霞
许多养猫狗的家庭都会自称自己是宠物的“爸妈”,我不是二毛的妈,二毛有妈。
二毛去年3月27日被汽车撞瞎了。大半年过去了,二毛已经习惯了黑色的世界。以我家为圆心,方圆一百米的地盘,它都留下了它的记号,所以,但凡它在路上走,是走的直线,而且转弯时不迟疑,基本看不出它是个两眼瞎的狗子。只是一旦路上来了车,远远的,它听到发动机声音,会紧张地躲在路边草丛中,不敢贸然动弹。
二毛妈的家与我家隔着一户人家,二毛遛弯时也会从它妈家后面经过,但显然它妈是不打算认这个狗儿子的,因为它妈又生了个“嫁不出去”的狗妹妹,母女俩总是一起在路上晃荡,有家,但爱不多,饱一顿饿一顿的。之前二毛妈经常来我家“扫荡”二毛的狗粮,那时候二毛的眼睛还没瞎,二毛从来不咬它妈。自从二毛瞎了,它妈好像就没来过我家,是因为多了个“拖油瓶”不方便了,还是其他原因,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我常常看到黑白花二毛妈和它的全黑“闺女”一起在路口垃圾桶边扒拉。
二毛妈性情温和,从没见过它追咬路人。每次见了它,我都会主动和它打招呼:二毛妈,你好呀。久而久之,我每次路过它家屋后,二毛妈都会笑眯眯地摇着它的尾巴,仪态万方地走到我身边,还顺带抬起它的一只前爪。如此礼貌的狗狗,我怎敢怠慢?每次我都会蹲下来,也伸出我的——我的手,和它亲切握手:你好啊,二毛妈。
然后,它带着它的闺女,摇头摆尾继续去找垃圾桶,我走我的路。
是的,我不是二毛妈,二毛有妈,而且是个温柔礼貌的妈。每个人都会溯源自己的来路,就算是一条狗,它也是有它的妈。至于爸,这事情就不好说了,太复杂了。
这些天我去街上不开车,绿色出行,完全靠两条腿,就在乡间小路上走,而且是田间小路。冬天,田野萧条,麦苗趴在地表,安安静静地蛰伏着等待春天。路边的野草枯黄着,有着暖阳的质感。好些天没下雨了,小路上泥土坚实,因有野草的枯叶和根系铺陈,漫步在乡间小路上,有一种脚下生根的感觉。
一百米处住户里有狗跑出来了。的确,在一片空旷的田野里突兀地出现了一个行走的人,狗们是要履职的。一条,两条,三条。三条狗向我奔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吠着。我倒不紧张。会叫的狗,一般不咬人的,咬人的狗是不会虚张声势吠叫的。我依然慢悠悠继续前行。前面的路边,依次站着五条狗,三条奶白色的,一条花的,一条黑的,是前面一百米那排住户家养的。这些天我每次路过,它们都要“问候”我,从一开始的吠叫,到慢慢认识,熟悉,到见了就摇尾巴,甚至俯首求撸脑壳,这个时间过程并不长。
后面追过来的三条狗停住了脚步,前面站着的五条狗表示了友好,并没有冲过来掠过我,与来犯者决斗。双方狗狗们用它们的交流方式进行了沟通,迅速散开,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农户人家养狗基本散养,人自在狗自由,当然,狗狗们的寿命也堪忧,尤其是冬天到了,不良狗贩会在月黑风高夜出来投药,然后捡死狗剥狗皮卖狗肉。过分的自由是有风险和代价的。
我不是二毛妈,但我会为它的疼而疼。我爸总会私自将狗放出院子,等我起床后呼唤它们,它们倒是跑得快的,一会儿就能回来进了院子,但总是隔三差五有意外。大前天回家后的二毛右眼皮流血了。是的,它是个瞎子,它左眼球没了,右眼睛瞳孔放大了,也是瞎的,但它有眼皮啊,不知道它在哪里怎么弄的,右眼皮那里破了,鲜血染红了眼眶周围奶白色的毛毛。我找来三七粉,蹲下来,托起它的脸,心疼地问它:“二毛,你怎么又被咬了?”前天,它的两条后腿弯处又没皮了,疼得它一天都不肯离开狗窝,不吃不喝的。没办法,我只能将肉撕碎了在它狗窝边喂它。
问它是被谁咬的,二毛不回答我。它没办法回答我。它是个瞎子,看不见这个世界,也不知自己是被什么样的狗咬的。大部分时候我是会陪着它们散步的。邻居家有条大黄狗,体型有三个二毛大,只要它站在路上,花花就会瑟瑟发抖,绕道走。二毛看不到,但它能感觉到危险,无知者无畏,它偏向虎山行,冲过去要与大黄撕咬。被我遇到一两次,我直接操起木棍或砖头就砸向大黄。自此,大黄看到我,也是绕道走。
狗与狗的问题的确应该交给狗们自己去处理,我不是二毛妈,怎么说都不应该掺和进去,但是,打狗还看主人面呢,欺负我养的狗,就是欺负我,无论对方是人,还是狗,我都不会开心。但没有我在身边的时候,二毛是一定会吃亏的,它是个瞎子,还生得那么弱小。
但是,只过了一天,二毛又跑出了院子。看着被我叫回来的它提着一条后腿一瘸一拐,我心疼,结果我爸告诉我:它在外面大路上跑得飞快,回来就不行了!我偷偷一观察,还真是的,没人的时候二毛四腿着地,健步如飞,一旦听到或者感觉到家人在不远处或身边,它立即就瘸了,就变成铁拐李了!
显然,二毛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老实和弱小。
我嫂子天生不喜欢猫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这不奇怪。嫂子每次看到二毛和花花,是面露嫌弃的,是避而远之的。之前我心里是不舒服的。前天我去嫂子家,抬头看到她新烫的头发,真是一言难尽,我都不想说,奈何她一定要从我这里得到评价。赶巧二毛从田地里拉屎回来,听到我的声音,它仰着小脑袋,方向不明地等着我的摸头杀。我低头看着二毛一身的羊毛卷,弯腰摸摸它覆盖着小卷毛的脑袋,笑着说:二毛,你舅妈的头发和你同款呢。
嫂子低头看看二毛,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是的呢,而且我的比二毛的还要卷。
我嫂子是二毛舅妈,我父亲是二毛爷爷,至于二毛到底怎么称呼我,不重要。反正它也不会说话。只要我记着二毛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就行了。